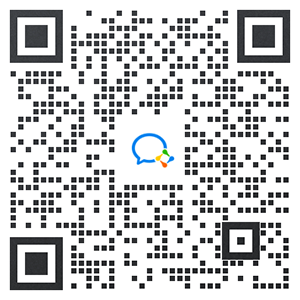【佛教讲堂】荷花意象和佛道关系的融合
发布时间:2015/7/13 11:36:52
![]()
荷、荷花,又名莲、莲花,是中国文学中最常见的花卉意象之一,具有丰富的内涵。莲花是佛门圣物,具有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寓意;在道教中,荷花的地位也是鲜出其右者,充满了祥瑞色彩。
印度佛教是着重探求解脱人生苦难的宗教,其基本的理论模式是:此岸———渡达———彼岸。“此岸” 即现世,是苦海;“彼岸” 即来世,是佛国。在印度佛教中,“彼岸”被描绘成一个美妙的世界,如《华严经》就精细地描绘了“莲花藏”世界;而佛教所宣扬的解脱、渡达过程是从此岸到彼岸、从尘世到净界的过程,则恰似莲花从淤泥中生。所以,佛经中常用莲花为比喻,如《大智度经· 释初品中尸罗波罗密下》:“譬如莲花出自淤泥,色虽鲜好,出处不净”;《无量寿经》“清白之法最具圆满……,犹如莲花,于诸世间,无染污故。”
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均已证明,荷花是原产于中国的古老花卉。中国的神仙传说在描写仙境时,也出现了荷花意象:“神芝发其异色,灵苗擢其嘉颖。陆地丹蕖,骈生如盖,香露滴地,下流成池,因为豢龙之圃”(《拾遗记》卷一“炎帝神农”);“ 有石蕖青色,坚而甚轻。从风靡靡,覆其波上。一茎百叶,千年一花。……故宁先生游沙海七言颂云:‘青蕖灼烁千载舒’”(《拾遗记》卷一“轩辕黄帝”)。而藕则是神仙的食物,葛洪《尔雅图赞· 芙蓉》:“芙蓉丽草,一曰泽芝。泛叶云布,映波赮熙。伯阳是食,飨比灵期”(《全晋文》卷一百二十一)。“伯阳”即老子,葛洪将老子之享高寿归于食藕之功。
荷花的花、食两途共同推进,形成“合力”;南北朝时期,随着道教的成熟,荷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“道瑞”的象征,江淹《莲花赋》即云:“一为世珍,一为道瑞”,他在《访道经》诗中亦有“池中莲兮十色红”之句。隋炀帝《步虚词二首》亦云“芳莲散十丈” 。《步虚词》,《乐府诗集》卷七十八引《乐府解题》:“《步虚词》,道家曲也,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。
道教是本土宗教,形成于东汉中叶;佛教是外来宗教,两汉之际传入中土。佛、道并存之日既远,两者之间的攻讦辩难、渗透融合就一直是研治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致力的课题。荷花兼具佛门圣物与道瑞属性两重“身份”,笔者在研读荷花资料时,发现在佛、道思想的动态关系背景之下,荷花的两重“身份” 不再是泾渭分明,而是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 。关注荷花“身份” 的微妙变化或可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佛、道之间的关系。本文即提供几个例子。
一、“莲台”与“生莲”
道教的来源之一是先秦时的道家思想,大约在东汉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。关于老子最早的坐势,史籍中没有明载。当佛教传入中土之初,道教对之攻讦,认为佛教是老子所创,这或许就是鲁迅先生所批评的中国人根深蒂固的“精神胜利法” 。《后汉书》卷三十下《郎顗襄楷列传第二十下》:“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”;西晋时道士王浮又作《老子化胡经》。《老子化胡经》今有残卷,叙述老子带领尹喜到西方教化各国,至罽宾国。国王逮捕了老子及其徒众,置于柴火之上焚烧。老子身放光芒,和尹喜等在火中,坐在莲花之上,读《道德经》。老子“ 入夷狄为浮屠”,安坐于莲花之上,很明显是来自于佛教的启示。至迟在唐代,老子已安坐于“ 莲台”之上。卢仝《忆金鹅上沈山人二首》:“ 太上道君莲花台,九门隔阔安在哉”(《全唐诗》卷388)。“莲台”本有特指,《法苑珠林》卷二十:“故十方诸佛,同出于淤泥之浊,三坐正觉,俱坐于莲台之上。”又如无名僧《禅诗》:“清莲台上见天唐,众生真心礼肆芳”(《全唐诗补逸》卷18)。从“太上老君莲花台”的定型,我们可以看出,佛教对道教的渗透。
当然,这种渗透是双向的。《关令尹喜内传》载:“关令尹喜生时,其家陆地生莲花,光色鲜盛”,尹喜是老子的弟子;陆地生莲亦见于《拾遗记》卷一“炎帝神农”:“陆地丹蕖,骈生如盖”;江淹《莲花赋》:“验奇花于陆地” 。在佛经中,也有“生时”“生莲”的记载。佛陀降诞前,净饭王宫殿内的四时花木,悉皆荣茂,池沼内突兀盛开大如车盖的奇妙莲花。虽然模式相同,但一为中国式的陆地生莲,一为印度式的池沼生莲,两者本有细微区别。但是,在流传过程中,易滋混淆。如《旌阳宫铁树镇妖》:“一是释家,是西方释迦牟尼佛祖,当时生在舍卫国刹利王家,放大智光明,照十方世界,地涌金莲花”(《警世通言》第40卷)。从用典的角度来看,“地涌金莲”是误用;但是,我们却可以看出道教对佛教影响的痕迹。
二、“藉芙蓉于中流”
公元402年,慧远在庐山“建斋立誓”,刘遗民誓文曰:“ … …藉芙蓉于中流……”,文中出现了“芙蓉”一词,好事者或据此附会出“莲社” 之说。佛陀成道后,转法轮(布道)时所坐的座位称之为“莲花座”,相应的坐势叫“莲花坐势”;在印度的转法轮雕像中,也有佛陀端坐于池中莲花之上的图案。但我们细按佛经,却从未有过“藉芙蓉于中流”的记载。这句表述是属于“本地风光”,来自于神仙、道教的启示。藉,坐卧其上曰藉。《文选》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:“藉萋萋之纤草。”李善注:“ 以草荐地而坐曰藉。”《拾遗记》:“汉武时,有人义角,面如玉色,美髭须,腰檞叶。乘一叶红莲,约长丈余,偃卧其中,手持一书,自东海浮来… …”;《真人关令尹传》:“老子曰:`天涯之洲,真人游时,各坐莲花之上。'… …” 。乘红莲自东海浮来或坐莲花游天涯之洲才是真正的“藉芙蓉于中流” 。此外,芙蓉、莲花同为荷花的别称,但是在佛教中通常称之为莲、莲花;而芙蓉则带有南国色彩,如《离骚》中的“搴芙蓉兮木末” 、“ 集芙蓉以为裳” 。按诸以上两点,“藉芙蓉于中流”的神仙、道教色彩可能要殊胜佛教色彩。这并不足怪。从接受的角度来看,在佛教尚未流行之时,以道喻禅是一条易于理解、易于接受的捷径。慧远在宣讲《般若经》时,“实相”概念难以演绎,就引《庄子》以类比,如风靡草,听者昭昭。在中国文化史上,在接受外来事物时,经常采用类似的权宜之计,其例子不胜枚举。
三、“青莲”
青莲,据《辞海》的解释:“本指产于印度的青色莲花。梵文名Utpala ,音译为`优钵罗' ,意译为青莲。”佛教常用青莲比喻眼睛,《维摩诘所说经》:“目净修广如青莲” 。又常用以说明佛法之清净圆满。如《涅槃经》卷二十四:“如水生花中,青莲花为最,不放逸法亦复如是。”唐诗中“ 青莲”一词常与佛教相关。如綦毋潜《宿龙兴寺》:“白日传心静,青莲喻法微”(《全唐诗》卷135);李白《僧伽歌》:“此僧本住南天竺,为法头陀来此国。戒得长天秋月明,心如世上青莲色”(《全唐诗》卷166);李群玉《法性寺六祖戒坛》:“ 惊俗生真性,青莲出淤泥”(《全唐诗》卷569)。
青莲是释氏常典,但当我在考索这一常典时,却发现其语汇是来源于神仙、道教,中土早有。如《淋池歌》:“凉风起兮日照渠,青荷昼偃叶夜舒”;《拾遗记》卷一“轩辕黄帝”:“ 有石蕖青色,坚而甚轻。从风靡靡,覆其波上。一茎百叶,千年一花。……故宁先生游沙海七言颂云:`青蕖灼烁千载舒'”;江淹《莲花赋》:“发青莲于王宫,验奇花于陆地。”晋崔豹《古今注》亦记载有青色莲花:“芙蓉,一名荷花,生池泽中,实曰莲,花之最秀异者。一名水芝,一名水花。色有赤、白、红、紫、青、黄,红白二色最对,花大者至百叶。”[ 2] (245)青莲“ 千年一花”,成为道瑞之物。在中国文学中,青莲又常称碧莲、碧芙蓉。司空图《送道者二首》:“洞天真侣昔曾逢,西岳今居第几峰。峰顶他时教我认,相招须把碧芙蓉”(《全唐诗》卷633);“桥边曾弄碧莲花,悄不记人间今古”(《全宋词》第4052页,中华书局1999年版)。
可见,青莲既是释氏常典,亦是道教典故。道教典故是先有之义,释氏常典是后起之义;后来居上,但前者并未退出,如鲍溶《长安旅舍怀旧山》:“青莲道士长堪羡,身外无名至老闲”(《全唐诗》卷487);王昌龄《河上老人歌》:“河上老人坐古槎,合丹只用青莲花。至今八十如四十,口道沧溟是我家”(《全唐诗》卷143);朱庆余《逢山人》:“星月相逢现此身,自然无迹又无尘。秋来若向金天会,便是青莲叶上人”(《全唐诗》卷515)。很显然,诸诗中的“青莲”都是道教含义。
至此,笔者多年来关于李白“青莲居士” 之号的疑问涣然而解。“青莲”是释氏常典;“居士” 之常义又是指居家修佛之士。李白取“青莲居士” 为号,似乎是佛教“因缘”;但这与李白的生平却格不符。李白虽然也曾受佛教的影响,但是综观其一生,道教才是融铸、造就他独特个性、独特诗风的主因。所以,“青莲”应该用的是道教典故;居士也不能泥解,而仅指高洁之士。“青莲居士” 作为夫子自道,在李白的诗中出现过一次,《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》:“青莲居士谪仙人”(《全唐诗》卷178)。“ 谪仙” 就是一道教神仙概念, [ 2] (167、174)换言之,“青莲居士”也是一道教称谓。其实,唐人也是将李白的“青莲居士” 看作一道教称谓的,谭用之《寄左先辈》:“学取青莲李居士,一生杯酒在神仙”(《全唐诗》卷764);杜光庭《读书台》:“山中犹有读书台,风扫晴岚画障开。华月冰壶依旧在,青莲居士几时来”(《全唐诗》卷854)
佛教青莲(优钵罗花)与道教青莲不仅在寓意上有别,在形态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花卉。岑参给我们留下了唯一的、弥足珍贵的资料。《优钵罗花歌》:“参尝读佛经,闻有优钵罗花,目所未见。天宝庚申岁,参忝大理评事,摄监察御史,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。自公多暇,乃于府庭内栽树种药,为山凿池,婆娑乎其间,足以寄傲。交河小吏有献此花者,云得之于天山之南,其状异于众草,势嵔如冠弁,生不旁引。攒户中折,骈叶外包,异香腾风,秀色媚景。因赏而叹曰:`尔不生于中土,僻在遐裔,使牡丹价重,芙蓉誉高,惜哉!夫天地无私,阴阳无偏,各遂其生,自物厥性,岂以偏地而不生乎!岂以无人而不芳乎!适此花不遭小吏,终委诸山谷,亦何异怀才之士,未会名主,摈于林薮耶。'因感而为歌曰:白山南,赤山北。其间有花人不识,绿茎碧叶好颜色。叶六瓣,花九房,夜掩朝开多异香,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。移根在庭,媚我公堂。耻与众草之为伍,何亭亭而独芳。何不为人之所赏兮,深山穷谷委严霜。吾窃悲阳关道路长,曾不得献于君王”(《全唐诗》卷199)。岑参在作品中,仔细地描述了优钵罗花的产地、形状以及作者的感慨。“使牡丹价重,芙蓉誉高”,优钵罗花非荷花(芙蓉)毋庸置疑。“优钵罗”是陆生,荷花是水生;“优钵罗” 接近于树,而荷花是花卉,贯休《闻迎真身》:“ 可怜优钵罗花树,三十年来一度春”(《全唐诗》卷836)
而在后代,佛教青莲与道教青莲不仅仅在形态上混为一花,而且在寓意上也渐渐互渗、含混,如贯休《道情偈》:“优钵罗花万劫春”(《全唐诗》卷835)。“万劫春”本非印度青莲(优钵罗花)题中之义,而是道教青莲“千年一花” 、“千载舒”之义。
四、“把芙蓉”
李白《古风》:“西岳莲花山,迢迢见明星。素手把芙蓉,虚步蹑太清……”(《全唐诗》卷161)、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:“遥见仙人彩云里,手把芙蓉朝玉京”(《全唐诗》卷173)、司空图《送道者二首》:“峰顶他时教我认,相招须把碧芙蓉”(《全唐诗》卷633),三诗在描写求仙时,都出现了“ 把芙蓉”这样一个动作。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中描述“高古”时也有“畸人乘真,手把芙蓉”之句。有趣的是,宋人为李白“ 写真”,也是手把芙蓉,崔敦礼《太白远游》:“遥见仙人于彩云兮,把芙蓉于玉京”(《全宋诗》第38册,卷2106)。“芙蓉”固为道瑞之物,但是“手把芙蓉” 却是标准的“舶来品” 。在印度阿旃陀壁画中,有一幅著名的《持莲花的菩萨》,菩萨(或云观音,或云文殊)右手持一朵莲花;观音的标准像也是头戴天冠,结跏趺坐,手中持莲花或结定印。仙人持芙蓉当是菩萨持莲花之移植。中国道教“八仙” 中的何仙姑也是手持荷花。“荷”谐其姓“何”,这个“造型”很显然也是来自于佛教菩萨的影响。
五、“火生莲”
火生莲,本是佛教语,语出《维摩经· 佛道品》:“火中生莲花,是可谓稀有。在欲而行禅,稀有亦如是。”故,火生莲比喻虽身处烦恼而能解脱,达到清凉境界;或用以比喻稀有之物。唐白居易《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》:“ 浮荣水划字,真谛火生莲”(《全唐诗》卷442)。释大观《远法师陆修静赞》:“古不可挽,今不可招。火生莲花,雪长芭蕉”(《全宋诗》第62册,卷3267)。“ 火生莲”又作“ 火中莲”,罗虬《比红儿》第三十五:“ 雕阴旧俗骋婵娟,有个红儿赛洛川。常笑世人多虚妄,今朝自见火中莲”(《全唐诗》卷135);但是,“ 火中莲” 却被道教进行了“ 换骨” 。张抡《减字木兰花· 修养十首》:“ 五行颠倒。火里栽莲君莫□。□要东牵。引取青龙来西边。一阳时候,□□温温光已透。消尽群应,赫赤金丹色渐”(《全宋词》第1841页,中华书局1999年版);张继先《金丹诗四十八首》:“得事只烹身上药,痴心莫望火中莲”(《全宋诗》第20册,卷1197)。“莲” 被比喻成金丹,而“ 火中生莲”被比喻成炼丹过程。“莲” 之金丹寓意在唐代即已流行。如:
许浑《庐山人自巴蜀由湘潭归茅山因赠》:“ 太乙灵方炼紫荷,紫荷飞尽发皤皤”(《全唐诗》卷535)。
陈陶《豫章江楼望西山有怀》:“ 终日章江催白发,何年丹灶见红蕖”(《全唐诗》卷746)。
贯休《山居诗二十四首》“ 二十一”:“ 石垆金鼎红蕖嫩”(《全唐诗》卷837)。
吕严《直指大丹歌》:“ 金鼎开成一朵莲”(《全唐诗》卷859)
“火中生莲”的道教寓意又是道教借鉴佛教语汇的例子。
六、“七宝莲花”
七宝或七宝莲花本都是佛教术语。七宝,《法华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、《大智度论》、《般若经》中均有不同的说法。七宝莲花,本指白莲(芬陀利花)、红莲(波头摩花)及其他五种睡莲。但在后来道教术语中也出现了七宝、七宝莲花的名称。如:
杜光庭《通玄赞八首》:“ 九光生院草,七宝满池莲”(《全唐诗续拾》卷51)。
杜光庭《七真赞》:“ 自然生七宝,人人坐莲花”(《全唐诗续拾》卷51)。
陈楠《金丹诗诀》:“ 天上七星地七宝,人有七窍权归脑。七返灵砂阴气消,铅炉只使温温火”(《全宋诗》第28册,卷1631)。
许及之《游三茅忽得佳处,留赠乡黄冠师》:“ 三茅观里仙为宅,七宝山头玉作堆。不尽经行奇特处,只教留作等闲来”(《全宋诗》第46册,卷2458)。
何处厚《游洞霄》:“ 七宝蜡炬光如银,凤泉饮散醉醺醺”(《全宋诗》第72册,卷3769)。
从上面的语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,佛教与道教之间在对立之中又互相接受了对方的影响。这种影响是双向的,但除了“青莲”与“藉芙蓉于中流”两例是佛教接受道教影响外,其余四例均是道教接受佛教的影响。这符合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趋势,佛教在进入中土之初,为了宣传教义,要采取一定的“宣传策略”,向中国的本土宗教借鉴语汇是一条可行之路。而隋唐之后,佛教发展成熟,其影响要超过道教。这从寺庙与道观、僧尼与道士、女冠数量的悬殊对比中即可见一斑。此时,佛教语汇反输给道教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。
荷花既是佛门圣物,象征“出淤泥而不染”,同时又是道教标识,充满珍祥色彩。在佛教与道教的融合、互动过程中,荷花充当了“信使”的角色。“三教调和”(或“三教合流”)是唐代思想史、文化史、宗教史的重要特色,论述者已多,精义胜解迭出。下面这则材料鲜见诸引用:
元和中,有高昱处士,以钓鱼为业。尝舣舟于昭潭,夜仅三更,不寐,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蕖,红芳颇异。有三美女各据其上,俱衣白,光洁如雪,莹若神仙。共语曰:`今夕阔水波澄,高天月皎,怡情赏景,堪话幽玄。'… … 又曰:`请各言其所好何道。'其次曰:`吾性习释。'其次曰:`吾习道。'其次曰:`吾习儒。'各谈本教道义,理极精微。(传奇· 高昱)[ 3] (1149)
这或可折射出唐代“三教调和” 的思潮,荷花是三者共同的载体。这大约就是后代所谓的“红花绿叶白莲藕,三教本是一家人”的先声吧!